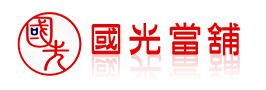(德國之聲中文網)有“天使手指”美譽的台灣鋼琴家陳瑞斌13歲就離開台灣的家鄉,獨自到歐洲學習音樂。他先在維也納音樂學院學習,然後到德國漢諾威音樂學院進修。在獲得最高演奏家文憑後,繼而向俄羅斯鋼琴大師貝爾曼(Lazar Berman)習藝,是貝爾曼唯一的亞裔弟子。16歲贏得意大利“拉赫曼尼諾夫”(Rachmaninoff)國際鋼琴大賽,成為最年輕的得獎者。之後屢屢在各個重量級國際鋼琴競賽中脫穎而出,比如在特拉維夫(魯賓斯坦)、華沙(肖邦)、鹽湖城(巴豪爾)、維也納、曼雷薩和意大利(羅馬、斯特雷薩)等。他在20歲之前就贏得5項音樂大賽的金獎。
德國之聲:您如何看待這次的巡演?疫情中的這場音樂會對你有任何特殊的意義嗎?
疫情稍減,我成為第一個出生於台灣的華人鋼琴家在德國演出,而且是巡演,意義非常重大。更重要的是,這個演出讓我有機會直接和當地民眾交流。疫情期間全世界舉辦音樂會的數量大幅減少。在德國,也因為疫情的關系,這次的演奏會只能讓25%的觀眾入場。盡管有種種不利票房的因素,德國主辦方並沒有取消我的演出,堅持舉辦音樂會,讓我更加珍惜。另外,石勒蘇益格-荷爾斯泰因(Schleswig Holstein)這個城市有個藝術節,我年輕時曾經參加過,現在有機會舊地重游,讓我非常開心。
德國之聲:您曾經說過,您在德國表演是帶著使命感,為什麼這麼說?
受到疫情的沖擊無全世界的藝術家大都法演出;而我卻有機會到歐洲巡演,其實很不容易。我這次演出的合約是一年多前簽訂的,主辦方一直沒有取消,所以我是帶著感恩的心情,要求自己一定要完美演出;而且因為我懂這裡的語言和文化,我相信,我和觀眾的音樂溝通會更直接;這次的客席指揮是一位羅馬尼亞非常著名的總監,而羅馬尼亞對我而言有它的歷史意義,因為我當年是第一個進到羅馬尼亞演出的華人。另外,我的老師的老師和拉赫曼尼諾夫是同學。我的老師也演奏過拉赫曼尼諾夫大部分的音樂而且留下錄音,獨缺第2號鋼琴協奏曲,也就是我這次要彈奏的曲目。這個曲目其實是當年我的老師在家裡私下教我的,完全沒有留下錄音。所以要聽這個曲目其實很不容易。我自己也很高興有機會再演繹它。
德國之聲:就您長期觀察德國音樂下來,您覺得德國音樂的特色在哪裡?
不管何種音樂風格,德國音樂的精神是:嚴謹、謙卑、專業、有內涵、不注重包裝;比起亞洲和美國音樂來說內斂得多。不管是弦樂拉出來的,還是管樂吹出來的音樂都是這種個性。這跟美國非常不一樣。德國人和法國人和俄國人也不一樣。而德意志民族吹出來的就是不一樣。德國人在音樂的表現就是這種特性。就我的觀察,疫情持續的兩年期間,大部分國家的音樂產業都斷斷續續的經營著,但是在德國幾乎沒有中斷過,德國人這樣的投入真的不簡單。
德國之聲:您13歲時獨自到歐洲學音樂,除了語言、文化的隔閡,您還得面對經濟上的窘境,飲食氣候的不適應等等。如今回想起來,這些遭遇對您而言是養分還是折磨?對音樂家而言是加分還是減分?
應該有百分之三百的加分。因為我離開台灣時,只有小學畢業,而且還不是音樂科班出身。結果我從16歲開始就參加各項國際音樂比賽。我的音樂基礎其實不很好,但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贏得比賽。我想,主要是德奧的環境、以及我經歷的磨練對我產生正面的影響。一直以來我覺得很累,一個人要處理所有的事情。我其實還有一個小我兩歲的弟弟,他後來也拿和我一樣的護照到奧地利學習音樂,拉中提琴。所以我不止要替他找琴,處理居留的手續,找監護人,也要替自己找監護人,因為我們兩人都還沒有成年。而且那個年代和現在非常不同,沒有網際網絡,沒有手機,只能依賴傳真。我經常外出參加比賽,往往來回要花上兩個月,等我回到維也納後,經常發現一地的傳真等我處理。這種情形持續10多年。
德國之聲:您有文化認同的問題嗎?您比較認同亞洲文化還是西方文化?文化認同對您的音樂重要嗎?
我比較認同西方文化,這項認同對我很重要,而且很深遠。我其實主要受到西方文化訓練和熏陶,直到近年才重新回頭去了解東方文化,然後想辦法促進東西方文化的交流。我的觀察是:一般人30-40歲以後才會開始對古典音樂產生興趣,而我如果只是像個工匠般准確的敲打鋼琴,只展現高超技術,這樣是無法感動他們。這就是為什麼我的老師經常逛博物館,而我也經常逛書店、博物館等等,因為我們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。
德國之聲:您認為亞洲人也可以很好的詮釋西方音樂嗎?
亞洲人悟性很高,但是往往有來自父母的壓力,而且很依賴網路。亞洲人彈奏法國音樂還好,因為法國文化對華人不這麼陌生,但是如果要詮釋德國音樂,往往缺乏德國的穩重和厚度以及它的內斂和含蓄。不是不會成功,但可能必須在德國待上20 到30年,才能在血液裡產生這樣的感覺,熏陶很久之後,再加上亞洲人特有的悟性和靈敏,也許會有不一樣的火花。
德國之聲:您近年來也會彈奏一些客家、閩南、台灣原住民或其他的音樂,比如黃河協奏曲、愛河協奏曲,為了尋根?為了豐富您的音樂內容?還是有其他原因?
以上的因素都是理由。作為華人,我希望推廣東方音樂,這是我的第一個訴求;而且從不同的素材可以找到創新,這一點在西方非常受到鼓勵的,他們對不同的文化和音樂非常感興趣。我做過不同的嘗試,也和不同的樂器合奏,都非常成功。西方人對新的素材非常渴望,他們基本上比華人更開放。我最近收到一個邀請,他們讓我的音樂和3D合作等等。至於如何讓客家、閩南這些不同文化融合,在這方面我有我的優勢。我也喜歡嘗試各種可能性,希望做出新的東西,這對文化交流和推廣都很有幫助。
德國之聲:音樂對您的意義是什麼?
音樂是我人生的全部,是我個人的歷史表達。有一天當我離開地球時,我到底留下什麼?我這個人的故事究竟是什麼?我可以和國際溝通,而且應該比政治的溝通更廣,因為音樂無國界。音樂家這個職業真的非常辛苦,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困難,它的投資報酬率真的很低,但是我不在乎投資報酬率,我在乎的是,在我離開地球後,後來的人如果看待我。我認為,當音樂家對我而言是正確的行業。我是屬於舞台的。
德國之聲:您現在上台前還會緊張嗎?還是您享受每一次的演出?
我每次上台前都還是非常緊張,但是如果准備充分的話,是可以非常享受的。不過我還是要感謝那些偉大的作曲家,如果我非常了解他們的音樂,就可以非常享受,甚至到忘我的境界。觀眾的反饋從我年輕時代到現在都相當多而且熱情。在台灣、在東歐、在俄羅斯、美國,即便德國也如此。這次我將彈奏“拉赫曼尼諾夫(Rachmaninoff)的第二鋼琴協奏曲”,其實我20多歲時在漢諾威參加畢業考試就是彈這一首曲子, 到了現在的年齡重彈此曲,心情非常不同。
德國之聲:如果您不當音樂家,您會從事什麼工作呢?
我會做類似的行業,包括傳承、宗教、社會工作者,一切可以影響社會的東西。教育、文化交流甚至改革,這些工作我都會去嘗試。我的重點不在於個人而是社會。所以從事音樂對我而言是對的行業,我喜歡影響別人,同時也想保有自我,音樂剛好提供這樣的可能性,這次的德國演奏會,我一次就可以和這麼多人交流,這是一件很快樂的事。今年的德國巡演之後,我還計畫在南德及美國、加拿大等地演出,2023年我會在歐洲與其他職業交響樂團合作巡演。
從2月8日至11日陳瑞斌將和德國石勒蘇益格-荷爾斯泰因交響樂團”(Schleswig-Holsteinisches Sinfonieorchester)合作演出,3個曲目分別是:
1)喬治·埃內斯庫的羅馬尼亞狂想曲 (George Enescu: Rumänische Rhapsodie Nr. 1 A-Dur op. 11/1)
2)謝爾蓋·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 (Sergei Rachmaninoff: Klavierkonzert Nr. 2 c-Moll op. 18)
3)讓·西貝柳斯的第一交響曲(Jean Sibelius : Sinfonie Nr. 1 e-Moll op. 39)
© 2022年 德國之聲版權聲明: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,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,不得擅自使用。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,並受到刑事追究。
作者: 邱璧輝